|
到了阆中文成,说上山的路修好了,可以坐车。但我还想走路,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
弯弯曲曲的路,连着高低起伏的山。
到了山顶,云就在脚下,茂密的灌木丛裹着云雾漫卷。
幺叔的孙三娃子在县城读书,陪着我。
“记得两边都是大树。”
“砍了。这几年山里的人都往城里走,就把家门前的树砍了。”
“可惜!好多都是几十年的老树。没人管吗?”
“自己种的,那个管,就连北垭口的那颗大树也砍了。”
“北垭口那颗大树也砍了?那颗树不是挂了牌的吗?”
“那是他们自己的树,先找村上要钱,卖给政府,村上说莫钱,他们就砍了。”
“唉!做劣呀!”
路过凤凰岭小学,一片破败景象,校门锁着,透过校门可以看见里面到处长着杂草。
“学校怎么这样了?”
“人都下山了,没人读书,前年就关了。”
墙上有块田家炳小学的牌,布满了灰尘。
到了大爸家,两三个小朋友围上来。
“五爷好!五爷好!”
“好!好!”
我便从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50元一张的新钱发给他们。
“为什么今年小朋友这么少?”
“大多人家都下山了。”
大爸大妈迎出来,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我拿了红包送上。
“回屋烤火,回屋烤火。”大妈说着。
“好!好!"
院坝扫的干干净净的,楼房也像刷过,还吊了两个红灯笼,门上有副对联:山门开接财神,旧岁去迎新年。两个纸娃娃抱着鲤鱼的剪子贴在上面。右墙壁还是挂着一窜窜玉米棒,墙角那两个燕子窝也还在,只是要等大年15过了,才出窝玩耍。
周围的亲戚都来了,才坐了两桌,6年前的席都摆到了院坝头,起码也是八、九桌。十几个小孩围着你,喊得好欢,一人发张压岁钱,前呼后拥的从这个山包,跑到那个山包,在学校的坝子头游耍,勾起阵阵儿时的回忆。
来时还做着这种想象,眼前却这般的凄凉了。
吃过晚饭,三娃子陪我去散步,。
西纳溪河绕着家的后腰淌出清脆的水声,却是显得清明。那脚边的石池,仿佛还有冉老师洗澡的倩影。
校操场的树越渐的粗壮了,地上的草都长了米深,只留出一条走人的路来。
“三娃子,元蹬老爹呢?”
“那边不是,年前11月死的。”
元蹬老爹那块自留地上起了个坟包包,那坟头还插着个花圈,只剩几片零碎的白纸飘着。
元蹬老爹是个五保户,那年他邀我赶七里场,走了4个多小时,上午10点去到下午3点才回来。场不大,还算热闹,卖鸡卖鸭卖蛋的摆在场上老房子的两边,场上还有小饭馆、小茶馆、理发店和杂货铺。
元蹬老爹在路摊开了两幅风湿药8块钱,我开的,还请老爹吃了盅小酒,下点鲁菜。
回家路上元蹬老爹走得好快,还哼起了山歌。
山路上碰见两娘母在树下囧着屁股阿屎。
“大屁股好白。”元蹬老爹说。
晚上,元蹬老爹捉来一只母鸡,我顾到塞给50元钱。
第二天中午,元蹬老爹又端来一盆豆腐,自己做的,我收了。
我老是记着北垭口那颗树,吃完饭我独自往北垭口。
远远望过去,过去是一株茂密的树挡在垭口,现在那垭口是空的,风从那里不停的灌进来。
翻过两道山,到了北垭口,垭口中央留下一个巨大的平树桩,直径有3米多长。
早年我到个这,常常被这巨大的树感动。
树叶遮蔽天日,树下有户人家,往来的路人累了,歇下来,去他家泡碗茶,小息片刻。
现在这间破败的房早已被惨烈的北风刮得只剩残垣断壁。
一个老乡从坡下过来。
“今天风好大!”老乡说道。
“老乡,他们为啥要砍树?”
“还不是为了钱。这树原是孙家祖辈种的,几代人了。孙家那几年挣了钱,搬进城前,他们找村上要7千块树钱,村上没给,他们就请人把这树砍了。真是害人呀!从此这儿的风比那儿都大,这山头也冷了很多。砍老壳的也该走霉运,进城第二年,他娃儿就得了白血病,到处借钱医。人说他得罪了树神,他还来拜,后悔不该砍这树。倒霉了才晓得。”
“老乡,这是啥树?”
“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是衫,有人说是榕,不过这树是很有些年头了。”
看着老乡被寒风吹得瑟缩的背影,我真的惊叹这些老乡们的举动,总想把祖辈的东西全带走,不留一点记忆。
这山上几十年的大树,在这些老乡搬家后都遭砍伐。60、70元一根,仅为这点小钱。
我们的村镇干部为什么就不管呢?
后来听说,贩运木材,正是这些村镇干部幕后在做。
------
很多新的植被又从山上长出来,要成才,还需几十年。
告别大爸,我和三娃子还走山路。
我忽然觉得这山里原来冷清了许多,但反而更美了。如果还有那些高大的植被耸立其间,让云朵穿行。
会有的,以后会有,只要那些黒手不再砍树。
我忽然又觉得要在这里安度晚年了!当个守山神。
我这样给大爸讲过。
回望凤凰岭上飘着的云朵,咱那么好看-----这里要来个守山神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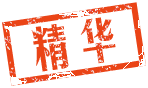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