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捉泥鳅。”
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吟唱,有童趣,有亲情,描绘了雨后捉鱼的如画场景:年少时,邻家的小妹妹,扑闪着大眼睛,洁白笔直的小腿肚,撒娇地跟在我们身后,要一同下河捉鱼。
而家住小河边的我,更是对此项“娱乐活动”喜欢有加,现在还时时回味其中的乐趣……
父母在我上小学时想方设法把房子从天天吵鸡骂狗的拥挤的川北客家老院中搬了出来,用两百只鸭子、半边猪肉和半年汗水为代价建成了临河大路边的五间瓦房。于是,这条叫神溪的小河便成了我儿时的快乐玩伴。
会看点风水的父亲说门前有河有路是吉利,更有他的那帮知青朋友把这个环绕房前的河牵强附会为“玉带”,屋后有山如轿,屋前有河如佩玉带,这个地形要出当官的。
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更多的是在这条河里捉鱼,而“玉带”好象一直到现在都与我没多大关系。
捉鱼的方式有“拊”鱼、摸鱼、钓鱼、毒鱼、电鱼、网鱼、罩鱼等几种。拊(音fu)是川北土话,是用工具把水舀干之意,也就是“涸泽而渔”,这多是在春秋季节,河水消落之际。摸鱼就是夏天下河在石洞石缝里摸鱼。毒鱼是用大量蚊香或药饵把鱼弄得晕头转向后用网捞或手捉——这多半又是冬天的行径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拊鱼,记忆中这方面的故事也多。
春秋之季,河水消减。放牛的时候,我便用竹杆或树枝在河汊水凼中乱搅,有时便看到大大小小受惊的鱼蹿来蹿去,鱼多之处,就是下手的地方。或在春天河鱼产卵时节,早晚我在河边转悠时,透过密实的芦苇,就能听见一些较大的鱼在水草和青苔较多之处产卵时拍打水面和水草时“噼噼啪啪”的声音。心动的我便叫上堂弟,拿上较轻的铁脸盆,扛上锄头,先在“侦察”好的河段上头取土扎好高大结实的围堰,再在下游扎个较平的堰,然后两兄弟便在下游撅着屁股用脸盆往外舀水,水干了鱼便自然变成了我们的桌上佳肴。
这是较顺利的情况。但更多时候这是个大而细却容易出“质量”问题的“工程”。并不是有鱼的地方都易扎堰,有的水流急,有的河汊深,有的不易取土。水流大时,还得顺河边开引水渠。有时上游已经扎好的堰坎底下会汩汩地冒水,得再去压实,乃至要下水去摸出漏水的地方。水快舀干时落差增大更容易漏水,也更危险,往往功亏一篑。那时多半已经看得到鱼在焦急地蹿来蹿去,连观战的兄弟都来帮忙挖土堵堰。稍幸堵好,往往又灌进半河水了。
拊鱼时,如果水凼不大,多是一个盆,站在水中舀水。这要弯腰驼背,煞是累人。冬天较冷,我们也有“发明”,用铁皮桶,在桶脚铁箍处用铁丝绑上两根绳子,再在桶耳上拴上两根绳子,然后两人站于两岸,左右手各执一绳,甩桶入水时桶口稍向下舀水,过了堰坎后提桶脚的绳倒水,这样一桶一桶地将水“挖”干。根本就是“人在河边不湿鞋”。就是冬天也不觉冷,有时还热得脱衣服呢。
用桶是较为“休闲”的方式了,更多的是站在水中舀水,常衣裤打湿,全身是泥,腰酸背痛。有时还不幸被石块或锄头划伤。
而在田中拊鱼,就很容易了。当然,田中捉鱼一般不是拊,又是“KANG”(音抗)了,就是用没有底的背兜,看准鱼游动的方向,去笼去盖去罩住,一旦罩住了,鱼大的就碰得背兜直抖动,那时,我们的小心脏也扑通扑通,然后捋捋额头上的汗水,不着急,伸手慢慢去抓住就行了。
小时候水田多,因为那里农村都兴关冬水田,春夏来临,养了一冬的鱼都膘肥体壮,产仔的时节,更是在田里蹿来蹿去,从浑水间或是浮萍下,划出一道道令我们心痒的波浪。但是,田是开阔的场地,鱼们总是和我们打“游击”,不易得手。于是乎,在鱼多的地方,或者我们几个人先吆喝赶鱼,然后飞快地用手掏田泥垒坎,形成围堰,然后把水舀干。因为田里的水是平的,也不深,又不存在上游流水,落差小,很轻松的,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拊鱼记忆最深的是,有次我一个人光着上身在太阳下舀了大半天水,其后两三天背上如同火燎,不敢粘床,后来冒出满背的水泡,最后整个背都可起下一层皮来。气得母亲好久都不许我出门下河。
除了拊鱼,热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下河逮鱼。大雨后水少了,我和伙伴们就只穿上小裤衩,扑楞楞扎进水里。顺河两边,从石洞或泥穴中探进去,多是双手并用,无处可逃的鱼们就被我们手到擒来。捉到的鱼用铁丝穿成一串挂在手腕上,或者用塑料袋、尼龙网袋装好用绳子系好袋口然后把绳子衔在嘴角,游动或者潜水都方便,最简单的是直接折一截树枝,留下一个倒钩,把鱼串
上。有时鱼也直往洞里钻,于是我们耐心地攥着它的尾巴把它们倒拖出来。这种方式捉到的以鲫鱼为多。而乌鱼生猛力气大,胡子鲢溜滑,都不肯轻易就犯。而冬天也有捉鱼的时候。冬天水清,多远都能见底,我们穿了胶鞋在河边观察,用脚一跺,有些鱼便会蹿动一下,游不了多远,就又钻入浅浅的草中。一旦发现有大的,很简单,我们在河边用树枝或竹杆,慢慢在把鱼往河边刨,冬天的鱼懒,你刨一下,它就随到动,慢慢地就过来了,待到近处,慢慢地用手去捉,或者干脆用一头剖成条状的竹杆或直接用竹耙把鱼扣到,拖到岸边就成了。乃至过年,没事时我们就地河边转悠,运气好时,捉个四五条,四五两一条,也是不错的收获,就养在那里,等下次再捉到凑多了,便成为一家人的美味佳肴。
我们那些水浅石头多的小河沟是不易钓鱼的。现在有一些背上蓄电瓶用电打鱼的,但我们小时候是几乎没有。现在毒鱼是不允许的,被发现是要被“理抹”的。因为是污染环境,破坏水源。但其实那时毒鱼主要是用药饵把鱼弄晕,然后用网捞。这个也很很诱人。哪里鱼多,知道有人毒鱼了,就去河里捞。有时看到正在水面换气的大鱼,裤子不脱就跳下去按。那些一二寸长的鱼们蹿上水面,游来游去,高高兴兴地抓半天,睡觉前,眼里都感觉有白花花的鱼在游来荡去。
有时场面也很壮观,有几次别人毒鱼后,我们从上游出发搜寻,便会发现在河道落差处,乱石嶙峋,水从石块间流过,很多的鱼白花花地躺在那些石块间,我们如鸭子一样扑下去,可是那些鱼们大半已经僵硬,甚至部分已经被鸟们啄食。然后我们捡起还有余温的或还在苟延残喘的,拿回家去用清凉水、盐水泡。往往我们勤快地换水,在瓷盆边观望,眼巴巴地期待他们能够尽早回过神来。
在回忆中,很多时会想到儿时的玩伴星。星和我是小学同学。那时大人们都说穿了女孩子的鞋跑不动路捉不到鱼,可是姊妹众多的他穿着他姐的鞋比我们跑得都快,也更比我们会捉鱼。冬天时,他空手出门,折一根桑树枝,从鸭子游过的冬水田边慢慢掠过,凭感觉判定鱼的方位,然后伸手下去捉,一早上就是十多条肥硕的鲫鱼,再用一头有倒枝的树条从鳃边穿了鱼,串成一串从我们面前晃晃悠悠地踱回家去,让我们咂嘴羡慕之极。
小学到初中我的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经常下河捉鱼耽搁时间父母亲也不多管我。上初中后,我还常常捉鱼,有时也送给大爸他们。记得还拿给一个老婆婆两三斤鱼,她当时硬给了我两角钱,我也收了。因为我觉得毕竟大部分算是送了她,这两角钱算是我劳动的象征,这就象摸鱼时凶狠的乌鱼(蛇鱼)或大鲤鱼把手臂弹得生疼的惊喜和快乐,是一种难得的回忆。
“鲤鱼头、鲢鱼腰,乌鱼脑壳你莫挑”,是说吃鱼的选择,而这三种鱼并不是很易捉得到。那时多是黄黄的土鲫鱼,剖时并不去鳞,下锅时用菜油或腊猪油一炸,两面金黄焦脆,令人口舌生香。也有时小鱼较多了,便索性不剖,一齐倒入汤锅熬到很浓,吃起来约略有点苦味,但反觉得更清香。但鲫鱼多剌肉薄,我并不是很喜欢。
乡人多说吃鱼不如喝汤,我也觉得就鱼汤煮的面条是最好吃的了,加之那时是手工作坊换来的面。而往往母亲碗中的面总是比我们的要少。我学着姐姐在端碗吃面前,总要少少地夹一筷子面条给辛苦的母亲,母亲用碗接了,总是笑着夸我说:“我儿子最有孝心了”。
再后来就离开老家在外读书,捉鱼就成了一种回忆。捉鱼的伙伴也久已不见。我原先在家乡上班时,回家多要买鱼提回去,经常做酸菜鱼,与父母家人一同吃。
而现在我在外地工作,没有买过鱼回家了,更好久都没有与母亲一同吃过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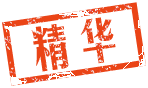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