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需 官
口述 吴仲叔 整理 肖卫兵 陈显福 韩松林
我叫吴仲叔,1921年6月21日出生,家住营山县小桥镇刺巴村。
小时候,我先后在小学和私塾读书11年。1939年7月,我到重庆考入了国民党军政部军需学校,学制3年。
在重庆读书期间,我经常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者杀我同胞、占我国土的文章,并亲身经历了1940年8月19日日军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次大轰炸致使2000多户居民房屋被毁,上万名市民伤亡,我也险些丧命。我在学校再也坐不住了,就与10多名同学向学校申请上战场抗击日寇。学校没同意,我就与其他同学上街游行、书写抗日标语、动员市民向抗日前线募捐。1941年6月5日,日军飞机再次对重庆进行了数小时的轰炸,造成了几千市民在防空洞边相互踩踏、在防空洞里窒息身亡的惨案。这更激发了我的抗日决心,我和同学们又向学校请愿,并用指血在横幅上写下了“投笔从戎,救国救亡”8个大字,然后将其悬挂在学校门口,学校最终同意了我和同学们的请战申请。
1941年9月,我穿上了军装,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西昌32军军需处,分到步兵3团任军需官,团长叫鲁行俊,后任团长叫郑仲可。在团部,我主要负责管理和押运前方将士的生活必需品。
我所在的团负责守卫和抢修一段几十公里长的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当时被称为国际“抗日输血管”,每天都有数百辆军车、公车和商车通行,日军经常出动飞机对公路和公路桥进行轰炸,纠集地面部队攻击运输抗日物质的车辆。
我所在的军需处到滇缅公路将近有200公里,再经过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才到我所在的守路团。每押送一次,往返需要两天,如果遇上日军飞机轰炸或地面部队攻击,往返的时间就更长,危险也更大。
有一天,我和3名押送人员满载一车粮食、罐头和压缩饼干刚上滇缅公路,就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我们马上把车开到一个转弯处,路边一侧的山坡上草木茂盛,正好遮蔽着我们的车。日军飞机在经过几轮轰炸后飞走了。守路部队正准备抢修公路,日军却发动了地面进攻,我与守路部队马上退到山上,对日军进行反击。日军的武器好,大都用冲锋枪,可以连发10多颗子弹,一个个就像亡命徒,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冲了上来。守路部队主要用轻机枪和手榴弹反击,我和其他3名押运人员用的全是短枪,射程不远,只有等日军靠近了才能打。这时,身旁有一位守路部队的战友牺牲了,我马上拿起他的步枪朝日军射击,正在爬坡的一个日军被我一枪命中,滚下了山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撤退了。我和守路部队马上对被炸的公路进行抢修,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修,车才能勉强通行。
像这样在押运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和地面进攻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天,我们的押运车在距守路团不到3公里处,又遇上了日军飞机轰炸,那天通行的车辆比较少,飞机在丢下几颗炸弹后飞走了,但我们的押运车着火了。我和其他3名押运人员立即上车扑火,我的双手被烧伤,头发也烤焦了,火被扑灭后,我们和守路部队又对公路被炸的弹坑进行了填补。车到守路团,卸下物品,我简单处理了一下烧伤部位,又马上驱车返回。
别以为我们军需处和押运人员吃穿不缺,其实不然。军需处每一样物品的收发都要逐一登记,逐一核实,不能有半点差错。我负责登记,物品押送到目的地,有专人签收,再将签收单带回核实。我们军需处和押送人员的吃穿远比守路部队差,军需处的罐头和压缩饼干很多,但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谁也没有吃过一次。我们军需处养了10多头猪,每个月杀一头,吃一次肉,其余时间连油腥都很少见过。
我们在押运途中,三、四个人带一口袋煮熟的洋芋,饿了就吃几根。有一次押运,滇缅公路上的一座桥被日军飞机炸了,守路部队抢修了几天几夜,我们把带的洋芋都吃光了,但桥还没修好。我们在车上饿得晕晕糊糊,有一位押运人员提出要拿几个罐头吃,我是押运组长,不能违反军规,就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山上找水喝,找野果吃,找不到野果就找野菜吃。到了守路团,团长郑仲可给我们每人奖励了一个罐头和几块压缩饼干,我没舍得吃,一直珍藏到抗日胜利那天。
我在军需处当了将近4年军需官,负责押运了几百车次物质到守路团,没出过一次差错。
日本投降后,我奉命到天津接收日军移交的战略物质,3个月后,回四川乐山军需处。1949年7月,我随部队向解放军95军投诚,在解放军部队,我是预备科员,也负责军需生活物质的管理和押运,先后参加了四川郫县、温江、灌县等9县的剿匪战斗。在管理和押运军需物质中,我先后两次受到师部的嘉奖。
1953年4月,我复员回家在县委统战部工作了几年,后由于精减人员和政历问题,被辞退回家务农,现享受抗日老兵相关待遇。
撰稿 韩松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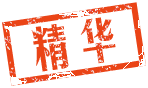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