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婆经常日绝我,说我脑壳少根筋,还经常短路。几十年埋头苦干,过了不惑之年才搞到个校长当。说是个校长,其实也只是好听点而已。一个学校两百多人,离县城将近一百公里,要转两到车还要前脚靠后脚地走一大截路。学校太小,搞不到着,自己的工资还要倒贴着用,不是老婆在县城做点小生意,这日子恐怕还将就不下切。
说起老婆,还不得不多说几句,她人长得不大好看,跟火柴棍似的,满脸蜡黄还点缀着不属于她这种年龄的斑斑,但她天性聪明,性格开朗,遇到大事小事总能逢凶化吉,所以我很是服她。 她常常对着我又吵又闹,完了后却反过来安慰我:“日绝是帮助,批评是爱护,烧壳子是望你进步”。唉!一个小女人,要起早摸黑地做生意,还要照顾七十多岁的老人和正读高中的儿子,也够累的啊!我当个两百多人的校长,却硬是要把它当成官来做,却硬是要发誓做出点成绩来,却把“每周一歌”都整不大明白,我这样的男人,又哪切找借口埋怨她的多话呢?所以她要打要骂也只能由着她了。
转眼之间,官都当了六七年了,扯着嗓子唱“每周一歌”也唱了六七年了,学校荣誉整了一大堆,但当初那点发誓要做出点成绩来的激情却褪得差不多了,只想动下窝,离县城能够近点,能给家里头多点温馨,给局长说了很多回却一直动不了,老婆又日绝我了:“别个说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你是不是该跑跑了?”跑啥子跑嘛?屁股勒门大个学校,请局长吃顿便饭一个学生娃儿都要摊五六块钱,我啷门跑嘛?
好不容易熬到局长换届,新局长体恤民情,上任不到半月就来到我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簸箕大的校园里走了一圈,也许是被学校良好的教育环境和井然有序的教学秩序折服了,他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不辛苦,不辛苦,感谢领导厚爱!”临别时,局长问我:“听说你在这里干了七年了,有什么困难吗?哪天到我办公室提出来嘛,能解决的我一定解决!”我脑壳一晕,感觉血往上涌,“困难?….就是……”还没说完,局长就接过来了“好好干,机会总是有的。”
送走局长,我就给老婆中了个电话,说我遇到贵人了,说终于可以挪窝了,说每周一歌可以改日报了……,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她连嗯都没嗯一声,半天才叹了口气,叭地一声挂了电话。
一晃两年又过去了,学校的人数从两百多变成了一百多人,局长没再来过,没再握过我的手,连电话都没主动给我打过,似乎把这个学校、把这个校长给搞忘了。我那每周一歌依然在唱,但已是声嘶力竭。老婆经常像是自言自语地问我:“你局长不是说有机会吗?啷门还没来嘛?”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放暑假前的周末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坐下来,电话就响了,是局长打来的:“晚上有空吗?辛苦了,过来坐坐,喝杯茶嘛!”
搁下电话,向老婆请示,没想到老婆激动得满脸通红,“快切,局长喊你搓麻将,多带点米米,给,五千。”“五千?这么多?”“唉呀,快切嘛!”出门前还反复交待,局长的牌割不得哦,还要看局长下什么叫,直接给他点起切,你千万不能赢局长的钱嚎!
来到那个叫什么“忽悠”的茶房,局长他们已到了,一个是他的堂兄,一个是他的老挑,三缺一。我毕恭毕敬地打了招呼,颤巍巍地坐下,局长说:“今天晚上杀家达子,打小点,就打个二加五嘛!”我也不懂什么叫“二加五”,搓起来再说。前四盘跟我无关,我没点炮也没割胡,只等他们结账。当他们把钱一数,我立马脑壳一晕,感觉血往上涌,起价两千,一番加五百,原来“二加五”是这个意思啊!
我心里慌得很,但毕竟当过这么多年的官,面子上还是得稳起噻,总不能让局长看出我的失态吧!摸摸裤包,这点钱开不到两盘啊!我扯个巴子上厕所,阴悄悄地给老婆发了个短信:“子弹不足,请求支援!”不到一会儿,就听到了敲门声,我晓得是援兵来了,拉开门,老婆把子弹塞进我的裤包:“两坨,给我麻起胆子搓!”回到桌上,颤巍巍地坐下,心一硬,脚一蹬,管他妈的,搓就搓嘛。
还好,虽然气质不够,但手气还不算太孬,两三个小时下来,一盘都没割局长的,我基本上整的是寡妇洗澡——自摸,虽然莫得几盘,也还算稳得起,只遭了几千大洋。正欢喜间,却听局长笑道:“哈哈,我摆了,一四七万”,我一看,我手上一四七万一样一对,每一张我都要得起,哈哈,我不得怕。一会儿,局长老挑说:“我也摆了,一四万。”转过来,我又摸上一张四万,刚轮到局长堂兄打牌,没想到他把牌一推:“我摸到一张一万下叫,我们看哪个手气好嚎,我也摆了,一四万。”我看了他们的牌,勾起指姆儿算了哈,一四万已经莫得了,铺子上只有两张七万,我就是摸到也可以成坎,不愁下不到叫。当然,这七万最好是让他两个下一四万叫的舅子切摸到,哪怕你两个龟儿摆得闹热。
在剩最后几张牌的时候,我果然又摸到了一张七万,下了个二五八条的通叫,哈哈,说不定你们还得给我点炮哦!
眨眼之间,桌上的牌只剩最后一张,该我摸,我心想,这张牌一定是张七万,我抓起来,果然是,没想到这独一无二的一张七万居然被我摸到了,我把四张七万扣在桌上:“我暗杠七万。”我把手一伸出去,却一哈木起了,桌子上莫得牌了,杠啥子嘛?嗯?杠啥子嘛?局长说:“莫得杠的了就莫法杠了,只有打噻!”打啥子牌哇?摆了的不能打,打其它哪一张都莫得叫,莫得叫是要赔三家的哟!“那就赔也,那就赔也”几爷子都叫起来了。我脑壳一晕,感觉血往上涌,妈那隔壁,这种牌局都让老子碰到了。
局长把牌一倒:“我是门清清一色,加摆……..”
我蔫搭搭地把钱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一家一家地给。剩下来的牌是啷门打的、钱是啷门给的、时间是啷门熬的,我脑壳里一片空白,当我把电话拿出来准备给老婆发短信请求再次支援时,局长发话了:“算了嘛,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嘛。”
回到家,我阴悄悄地躲进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象做错了事的学生娃儿面对老师一样面对老婆,把大半年工资被一夜洗白的过程全面向她做了汇报,没想到她听后捧着肚皮哈哈大笑,把眼尿水都笑出来了“哈哈,我搓了几十年的麻将都没碰到过这种牌局,你在哪里撞到的狗屎运哦,这样的机会也让你遇到了,你想不转运都不得行了!……哈哈,莫呕了,走,我们还是切唱我们的每周一歌。”那晚,我眯着眼睛没睡着,到天亮时还不断地听到老婆轻轻的叹气声。
一个月后,我调进了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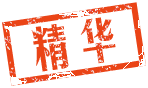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1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1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5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25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37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37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5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5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5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0:5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1:2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1:2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3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3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2:1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4:42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4:42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6:4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6:4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8:4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18:4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22:01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2 22:01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4 11:3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4 11:3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4 22:1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4 22:18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0:5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0:5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2:3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25 12:30
|
 楼主|
发表于 2011-4-30 20:24
|
楼主|
发表于 2011-4-30 20:24
|